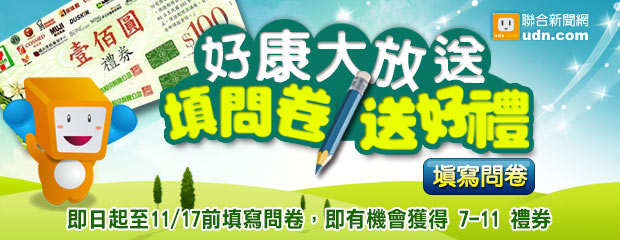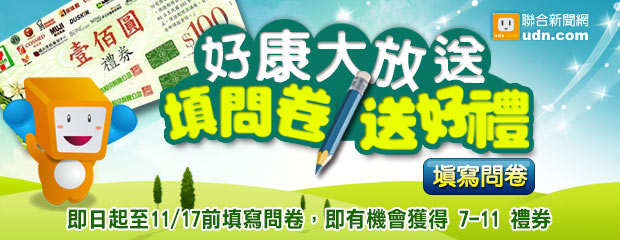科幻文學本來就是樂觀主義的文學……
常常有人對我說:「我不喜歡讀科幻小說,因為它講的都是未來世界虛擬的故事,和現實人生毫無關係!」真的是這樣嗎?
其實科幻小說一個很重要的主題,就是人如何安身立命?所以我就從安身立命談起,然後回顧科幻小說的過去並瞻望科幻小說的未來,最後「老張賣瓜、自賣自誇」介紹我最新科幻小說「海默三部曲」的第一部《多餘的世界》。
1.如何安身立命
華人不管身在何處,似乎都避免不了飄泊的命運,有時候是被動為了逃避戰亂,有時候是主動追尋更好的生活。往深一層次看,都是尋找安身立命的所在。
我有一位英年早逝的好朋友趙寧,他既會畫畫又能動筆。當年他最膾炙人口的就是漫畫配打油詩,有一首模仿王翰的〈涼州詞〉尤其傳誦一時:
葡萄美酒夜光杯
欲飲飛機馬達催
醉臥機場君莫笑
古來出國幾人回?
雖是打油詩,卻有鮮明的時代背景。過去的文人醉臥沙場是因為「古來征戰幾人回」,現在的學子醉臥機場則是因為「古來出國幾人回」,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確如此。
但留學生出國一去不返的現象不久就起了變化。首先在台灣出現了「歸國學人」的新詞。「歸國學人」本是褒揚的話,後來因為許多歸國學人表現不佳竟被視為「公害」,像過街老鼠般人人喊打。八十年代以後回去的人實在太多,阿貓阿狗都是歸國學人,台灣人見怪不怪,這些名詞反而被遺忘了。
在大陸也有過類似的變化過程。九十年代的海龜派回國就坐了直升機青雲直上。但經濟泡沫危機隨即發生,人人羨慕的「海龜」變成到處吃不開的「海鱉」。加上跟隨著父母回去的小留學生種種不適應,反而給大陸社會製造了不少問題。
近年又出現一種現象:回去的不再是學成回國雄心萬丈的「歸國學人」或「海龜」,反而是退休的老僑。這種現象尤其以台灣最為普遍。我曾經借用韋莊〈菩薩蠻〉的名句「未老莫還鄉,還鄉須斷腸」指出新的趨勢是「未老莫還鄉,還鄉須台獨」!
所謂「台獨」就是「回台獨居」的簡稱。如果夫妻都健在,多半會選擇留在僑居地。萬一有一方走了或者雙方離婚,單獨一個人留在僑居地沒啥意思,就會考慮還鄉定居。現在不再講究內在美(國)或外在美,而是內在天(堂)或外在地(獄)。
在台灣只要有個7-11,所有生活問題基本上都可以解決!所以從前喊:「一二三,到台灣,台灣有個阿里山。」現在則喊:「三二一,回嘉義,嘉義遍地七十一!」台灣的健保也辦得不壞。但最主要還是因為台灣的人文環境已經相當成熟,讓退休老人可以生活得很愜意,不會感到寂寞無聊。
然而黃美惠在「金山人語」專欄也坦白指出:台北的經濟成長遠遠落後鄰國,淪為一個「適合養老、不適合衝刺事業的城市」。「若你尚年輕、有才華,離開台北到上海或北京發展是比較好的選擇」。
其實人間處處有桃源。華人如何安身立命?是出走或是回歸?可以有各種不同的選擇。
2.科幻的過去和未來
無獨有偶,「如何安身立命」也是科幻小說重要的主題。不僅是科幻小說,在建築理論裡也有學者提出類似的看法。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席德班教授發明「生存美學」的理論,指出原始人為了躲避風雨和野獸必須躲到山洞裡,就是所謂的「隱蔽所」(Refuge)﹔但為了覓食打獵或收成,必須到空曠的田野去,就是所謂的「光明地」(Prospect)。
席德班教授認為東方和西方的建築,都包涵隱蔽所和光明地的對比。例如美國建築大師萊特(Frank Lloyd Wright)的重要作品強調明暗相間,往往通過黑暗的走廊進入光明的大廳。萊特的設計非常像蘇州獅子林明暗相間的走廊和大廳。不論是建築或其他藝術,到了哲學的境界往往東方和西方都是彼此相通的。
從小說的角度看,隱蔽所和光明地的對比就變化為回歸和出走的對比:人年輕時要奮發出走,邁向光明地﹔到了功成名就就想回歸鄉土故國,遁入隱蔽所。回歸和出走也就是人安身立命的兩種境界。
從西方和東方文化對立的角度看,西方人出走到心目中的光明地也就是烏托邦,東方人則回歸到嚮往的隱蔽所也就是桃花源。
荷馬的長詩〈奧德賽〉可說是古希臘人的科幻小說,敘述奧德賽和他的部下的漂泊故事。奧德賽離開他甜蜜的家園和美麗的潘羅普去攻打特洛伊城,城陷後卻又到處流浪了許多年。這是安身立命的兩種境界的弔詭:歌頌甜蜜家園的流浪者往往並不急著回家!
經典科幻電影《禁忌星球》(Forbidden Planet)改編自莎士比亞名劇《暴風雨》。飄泊的太空星艦是後來電視劇《星艦迷航記》的前身。禁忌星球的少女一心想跟隨她的戀人星艦艦長出走,而她的老父卻認為他已找到最後的家園。這是安身立命的兩種境界的衝突,最後的勝利當然屬於年輕的生命。
另一本經典科幻小說羅博•漢藍的《探星時代》(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)裡從地球出走探星的年輕人,竟發現他的太空船比後來出發的太空船走得更加緩慢,後發先至的太空船反而在目的地等他,所以他不是出走而是回歸。這是安身立命的兩種境界的妥協,也可看作「正、反、合」的辯證過程最後「合」的境界。
我還可以舉出許多類似的例子。我的第一篇科幻小說《超人列傳》是我出國第一年時寫的,探討的正是我在那時期思索最多的問題:人離開鄉土變成超人,如何安身立命?
科幻小說過去不大為華人世界所接受,但是這個情況正迅速改變。例如2013年美國新拍了一部科幻電影《重力》,女主角珊卓布拉克自己的太空船壞了,竟必須逃到中國的神舟宇航站求救。試想這種情況在二十年前可能發生嗎?現在華人世界的年輕人發現宇航不再是美國和俄國的專利,他們變得更有自信大步走出去。科幻文學本來就是樂觀主義的文學。近年科幻文學在大陸發展極為快速,我們樂觀其成。
3.回歸呼回世界
前幾年我有點消沉,少寫科幻小說,三年前才決定再度執筆。關於我這決定有個小故事:2010年我跑去看一部當年得獎的阿根廷電影《他們眼中的祕密》。這部電影無論攝影、劇情、主角演技以及地方風情都頗有可觀,尤其有句對白深深打動了我:「一個人可以改變姓名、地址、容貌和其他一切,卻改不了他的狂熱嗜好。」
看電影時我不斷在思考我的狂熱嗜好是什麼?我突然明白,不繼續寫,活著還有什麼意義呢?是回歸呼回世界的時候了!
呼回,西班牙語的拼法是Jujuy,英語拼作Huhui,是阿根廷北方一個偏遠的州。多年前我為了拜訪詩人作家波赫士的故鄉去布宜諾,意外發現阿根廷這個州和我筆下的呼回世界同名。我從人間世出走到科幻的呼回世界,但彷彿鬼使神差般,筆下的呼回世界原來真正存在!
有趣的是這部影片裡好幾次提到呼回,電影最後甚至有一段很重要的情節就是以呼回為背景拍攝的。我決定再度開始寫科幻小說《多餘的世界》,就在電影裡再度遭遇呼回世界。您說巧不巧?
(注:本文摘自作者在波士頓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年會的主題演講。)